华为云桌面服务器地址公司裁掉我,我拿走所有盆栽,第二天全公司电脑集体蓝屏_1
腾讯云服务器价格表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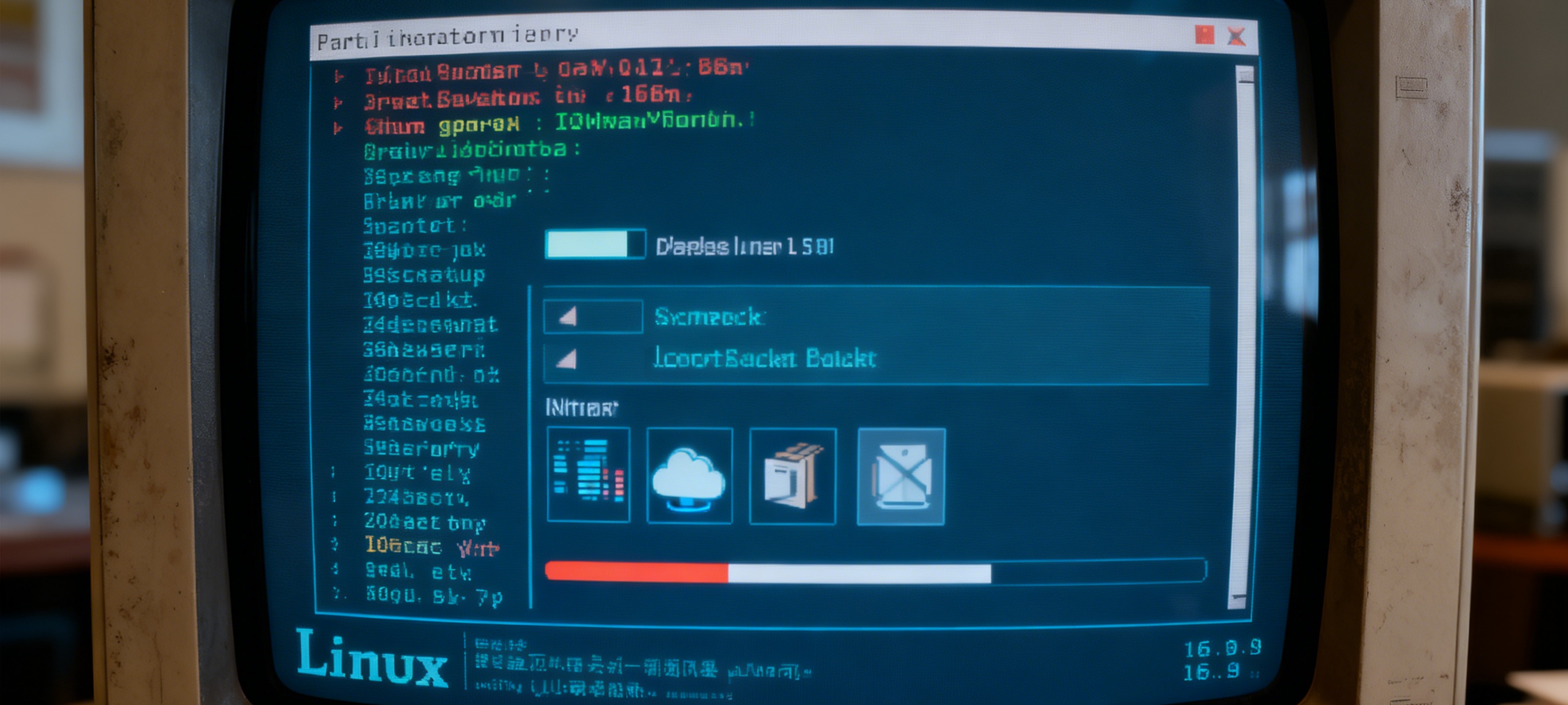
HR总监办公室的空调开得像西伯利亚的寒流。
我搓了搓胳膊,看着对面那个被称为雪莉姐的女人。
她姓什么我早忘了,反正公司里这种姐那种哥,都是些虚情假意的江湖名号。
雪莉姐脸上挂着一副精准计算过的惋惜,嘴角上扬十五度,眼神里却结着冰。
李未,她把我的名字念得像一道凉菜,公司最近的战略调整,你知道的。
我当然知道,不就是降本增效那套鬼话么。
翻译过来就是:老板想换新车了,所以你得滚蛋。
业务重组,架构优化,她继续背诵着那套仿佛AI生成的台词,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。
我盯着她桌上那盆小小的多肉植物,叶片肥厚,绿得有点假,一看就是塑料的。
真可怜,连生命都是伪造的。
所以,名单上有我?我问得直截了当,不想再跟她绕圈子。
她似乎对我这种不走流程的直接感到一丝不快,但还是维持着职业假笑。
我们综合评估了岗位匹配度和未来发展潜力……
得,别说了,我懂。
N+1赔偿方案在这里,你先看一下。我们也是争取到了最优的条件。她把一份文件推过来,纸张滑过桌面,发出沙沙的、令人心烦的声音。
我没看。
看什么呢?一串数字而已。
它衡量不了我在这家公司耗费的七年青春,衡量不了我为了项目上线睡在机房的那些夜晚,更衡量不了我为这家公司服务器集群亲手写下的每一行代码。
行,我签。我说。
雪莉姐愣了一下,大概是没料到我这么爽快。
她准备好的一大套安抚、劝说、软硬兼施的话术,瞬间堵在了嗓子眼,像一团湿透的棉花。
好的,那你在这里签字……她赶紧指着文件末尾。
我拿起笔,龙飞凤舞地签下自己的名字。
李未。
未,未来的未。
可我的未来,在哪儿呢?
签完字,我把笔往桌上一扔,发出啪的一声脆响。
东西我今天就收拾走。
按规定,交接完工作,明天……
我的工作不需要交接。我打断她,整个公司的网络架构图,在我脑子里。你们新招的人,让他自己慢慢摸索吧,就当是公司为培养新人付出的成本。
我站起身,没再看她那张精彩纷呈的脸。
走出办公室,冷气瞬间被走廊的暖气吞噬,我却觉得更冷了。
办公区里,同事们都在埋头敲键盘,但眼角的余光像探照灯一样,齐刷刷地往我身上扫。
他们都知道了。
这种事,在公司里传得比病毒还快。
我径直走向我的工位,那个被我打理得像个小型植物园的角落。
桌上,一盆文竹青翠欲滴。
显示器旁,一盆虎皮兰长得跟剑一样直。
窗台上,还有一盆我从奄奄一息救回来的龟背竹,叶片上的洞洞,像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这些,都是我的。
我开始拔掉电脑的各种线缆,把个人物品一件件装进纸箱。
键盘、鼠标、我那个用了五年的杯子、抽屉里没吃完的零食。
然后,我抱起了那盆文竹。
哎,未哥,你……旁边工位的小刘探过头来,一脸的不知所措。
小刘是我带出来的实习生,刚转正没多久,技术不怎么样,人倒是挺老实。
没事,我拍了拍他的肩膀,江湖再见。
我抱着文竹,走向了另一个角落。
那是行政部门的地盘,窗边有一大盆长疯了的绿萝,藤蔓垂下来快两米长,是我一点点养起来的。
我走过去,开始把那些藤蔓小心翼翼地收拢。
一个行政小妹看见了,怯生生地问:未哥,你干嘛呀?
它是我养的,我带走。我说得理直气壮。
可是……可是这是公司的财产吧?
公司买的时候,就是个快死的根,花盆钱还是我垫的。你要跟我算,可以,把雪莉姐叫来,我们连花盆带土,一克一克地称。
小妹被我唬住了,没敢再说话。
我把绿萝抱了起来,很沉。
接着是研发部的琴叶榕,市场部的金钱树,还有茶水间那盆谁也不管、被我用过期的酸奶救活的和平百合。
我像个搬家公司的工人,在整个办公区里来回穿梭。
每到一处,都抱走一盆绿色。
那些曾经死气沉沉的角落,因为我的存在而有了生机。
现在,我要把这些生机,全部抽走。
同事们的眼神,从最初的同情和尴尬,慢慢变成了惊愕和不解。
他们大概觉得我疯了。
被裁员的刺激,让一个平时还算温和的IT男,变成了一个偏执的植物大盗。
王经理,我的直属上司,终于坐不住了。
他从自己的独立办公室里冲出来,拦在我面前。
李未!你这是在干什么!他一脸的怒气,仿佛我刨了他家祖坟。
搬东西。我言简意赅。
你搬植物干什么?这些都是公司的固定资产!他指着我怀里的琴叶榕,唾沫星子都快喷到叶子上了。
王经理,说话要讲证据。我冷冷地看着他,公司资产列表里,有这盆琴叶榕的编号吗?采购单据呢?维护记录呢?
他噎住了。
这些都是我从花鸟市场,或者从网上,一点点淘换回来的。土是我买的,肥是我施的,虫是我杀的。它们对我来说,不是固定资产,是家属。
你……你这是胡搅蛮缠!
你要是觉得有问题,现在就去报警,我把脸凑近他,跟警察说,你们公司一个被开除的员工,偷走了十几盆花。你看他们立不立案。
我的声音不大,但周围的同事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诡异的寂静,只剩下服务器风扇的嗡嗡声。
王经理的脸涨成了猪肝色,他大概这辈子都没受过这种气。
一个即将滚蛋的下属,居然敢当着全公司的面,这么跟他叫板。
但他终究没敢报警。
这事传出去,丢人的是公司。
好,好,好!他连说三个好字,指着我,你行!李未,你给我记着!
我记性好得很。我抱着琴叶榕,从他身边挤了过去。
我叫了一辆货拉拉。
师傅到楼下的时候,我正吭哧吭哧地把第五盆植物搬进电梯。
公司前台看着我,眼神复杂得像一道高数题。
我一共搬了十六盆。
大大小小,高的矮的,把货拉拉的小货箱塞得满满当当。
师傅一边帮我固定,一边啧啧称奇:兄弟,你这是……花店倒闭了?
差不多,我笑了笑,新店开张。
坐在副驾驶上,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写字楼。
那栋我待了七年的玻璃盒子,在视野里越来越小,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影子。
我没有丝毫留恋。
只有一种报复后的、扭曲的快感。
回到我那个四十平米的出租屋,我才意识到工程的浩大。
十六盆植物,把原本还算宽敞的单间,挤得像个热带雨林。
龟背竹巨大的叶子伸到了我的床上,绿萝的藤蔓缠住了我的台灯。
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植物混合的、潮湿的气息。
我一屁股坐在地上,环顾四周。
我被孤立了。
被整个世界抛弃,只剩下这些不会说话的植物陪着我。
我拿起手机,点开招聘软件。
35岁以上网络架构师,请谨慎投递。
要求五年内一线大厂经验。
精通云计算、AI运维,有海外项目经验者优先。
每一条招聘信息,都像一记耳光,火辣辣地抽在我的脸上。
我的经验,我的技术,在一夜之间,好像都成了过时的古董。
焦虑像藤蔓一样,开始缠绕我的心脏。
我关掉手机,不想再看。
我开始给我的家属们挨个浇水。
水流过干燥的土壤,发出滋滋的声响。
我摸了摸琴叶榕宽大的叶片,又碰了碰文竹纤细的枝条。
它们的沉默,仿佛是一种安慰。
以后就靠你们了啊。我喃喃自语。
当然,我指的不是靠它们光合作用制造的氧气。
我走到那盆最大、最不起眼的琴叶榕旁边。
它的花盆是那种最廉价的塑料深盆,盆底的托盘上,常年积着一些灰尘。
我把手伸进托盘下面,摸索了一阵,抠出来一个用黑色胶带缠得严严实实的小方块。
那是一个树莓派Zero W。
一个极小、极便宜的微型电脑。
我把它藏在这里,已经快两年了。
不只是这盆琴叶榕。
市场部的金钱树、研发部的龟背竹、茶水间的和平百合……一共八盆关键的植物底下,都藏着这么一个小东西。
它们通过花盆底部钻出的小孔,用极细的电线连接着一个小小的传感器,有的监测温湿度,有的监测光照,甚至还有的监测空气中的挥发性有机物。
这些,都是幌子。
它们真正的任务,是通过办公室的访客Wi-Fi,悄无声息地,每隔3.7分钟,就向公司内网的核心服务器集群,发送一个加密的心跳包。
这是一个我独创的、从未向任何人汇报过的、物理环境安全监控系统。
我给它起了个名字,叫绿盾。
这个系统的逻辑很简单:IT设备可以被软件攻破,但物理安全同样重要。如果有人想从物理上破坏或偷窃服务器,必然会扰动环境。
而分布在整个公司、谁也不会在意的盆栽,就是我最好的监控探针。
这些心跳包,像一道道护身符,证明着一切正常。
而核心服务器的底层守护进程,被我写入了一条规则:
如果在48小时内,连续丢失超过80%(也就是至少七个)的绿盾心跳信号,系统将判定为重大物理安全入侵。
届时,将触发最高级别的安全锁定协议。
这个协议的表现形式非常……朴素。
它会直接锁定所有服务器的引导扇区,并在所有连接的终端屏幕上,显示一个蓝色的错误界面。
也就是俗称的,蓝屏。
我设计这个,初衷是为了安全。
为了防止商业间谍或者不满的员工,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溜进机房,拔走几块硬盘。
我甚至还设想过,如果哪天公司着火了,这些对环境敏感的探针也能提前预警。
我真是个天真的傻子。
我从未想过,第一个拔走硬盘的,会是公司自己。
而他们拔走的,是我。
我把那个小小的树莓派放在手心,它甚至还有点温热。
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。
距离我离开公司,已经过去了五个小时。
48小时的倒计时,已经开始了。
第一天晚上,我失眠了。
我的大脑像一个过热的CPU,疯狂地处理着各种信息流。
愤怒、不甘、对未来的恐惧,还有一丝隐秘的、即将大仇得报的期待。
我爬起来,在我的植物王国里走来走去。
这些植物,每一盆都有一个故事。
那盆龟背竹,是公司刚搬家时,前一家公司扔在楼道里的,叶子都黄了,是我把它捡回来,换土施肥,才救活的。
那盆金钱树,是市场部的小姑娘失恋时,一气之下要扔掉的,说看见它就想起前男友送的,晦气。我给它换了个盆,搬到了一个阳光好的地方,现在长得比谁都旺盛。
还有那盆和平百合,被保洁阿姨天天用洗洁精水浇,叶子都烧焦了。我把它抢救过来,告诉阿姨这玩意儿精贵,不能瞎伺候。
七年,我不知不觉,成了这家公司的园丁。
我不止维护着冰冷的代码和服务器,也维护着这些微小的、沉默的生命。
可公司不需要园丁。
他们只需要随时可以替换的螺丝钉。
第二天一早,我被手机震动吵醒。
是小刘发来的微信。
未哥,你走了之后,打印机老是脱机,怎么回事啊?
后面跟了一个哭泣的表情。
我盯着那行字,心里冷笑。
当然会脱机。
打印机服务器的IP地址分配策略,是和几个网络设备绑定的,其中一个路由器的管理权限,只有我知道。为了稳定,我设置了一个很短的租约期。
我离职了,密码带走了,租约到期,地址一变,打印机自然就失踪了。
我想了想,回复他:重启试试。
这是我们IT界最万能,也最敷衍的回答。
小刘很快回复:试了,没用啊!
那就再重启试试。我回。
发完这句,我把手机调成了静音。
我不想管。
我凭什么要管?
我用公司发的N+1,给自己叫了一顿丰盛的早午餐。
小笼包,豆浆,油条,还有一份奢侈的牛肉煎包。
我坐在我的植物中间,吃得心安理得。
阳光透过窗户,洒在龟背竹的叶片上,形成斑驳的光影。
真好。
这才是生活。
下午,小刘又打来了电话。
我犹豫了一下,还是接了。
未哥,救命啊!内网的共享盘,好多人都访问不了了!王经理快把我骂死了!他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共享盘。
呵。
那个权限管理系统,是我三年前自己写的脚本。为了防止权限滥用,我加了一个动态令牌验证,令牌的生成算法,跟某个特定服务器的CPU温度,做了一个非线性关联。
而那个服务器,因为散热不好,风扇策略被我手动调整过。
我走了,没人管它,CPU温度一上去,算法的参数就变了,令牌自然就失效了。
这事,除了我,鬼才知道。
你查一下日志,看看报错代码是什么。我故作镇定地指导他。
日志里全是乱码啊!未哥,你当时到底是怎么设计的?
时间太久,我忘了。我轻描淡写地说。
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,只剩下小刘粗重的呼吸声。
未哥,他突然压低了声音,你是不是……故意的?
我笑了。
小刘,饭可以乱吃,话不能乱说。我一个被开除的员工,我能有什么本事?我人都在公司外面了。
可是……
别可是了。你们现在有新的技术负责人,有王经理坐镇,我相信你们能解决的。加油。
我挂了电话。
心里那点对小刘的愧疚,很快就被一种复仇的快感所淹没。
活该。
你们不是觉得我可有可无吗?
不是觉得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我吗?
现在,你们就慢慢享受这个没有我的世界吧。
我甚至还有点闲情逸致,开始研究起了我的那些树莓派。
我把它们一个个从花盆底下拆出来,吹掉灰尘,接上电源和显示器。
屏幕上,熟悉的Linux启动界面闪过。
我敲下几行命令,查看它们的日志。
Connection failed. Target host unreachable.
Retrying in 3.7 minutes…
Connection failed…
它们像一群忠诚的、找不到家的信鸽,一遍又一遍地,徒劳地尝试着联系母体。
我看着这些日志,就像在欣赏一首后现代主义的诗。
充满了荒诞和悲凉。
晚上,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。
是之前关系还不错的一个研发部的老同事,大飞。
喂,李未啊,干嘛呢?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疲惫。
在家养花呢。
行啊你,心态真好。他顿了顿,似乎在组织语言,那个……公司现在有点乱。
哦?怎么了?我假装好奇。
不知道怎么回事,下午开始,测试环境的服务器集群,响应变得巨慢无比,跟瘫痪了差不多。大家都在加班查呢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这倒是在我的意料之外。
测试环境的服务器,跟我的绿盾系统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查到原因了吗?
没呢。王经理把锅甩给小刘,说他动了什么配置。小刘那孩子都快急哭了,跟我说他什么都没干。
王经理还是那德行。我撇了撇嘴。
谁说不是呢。哦对了,还有个怪事。大飞说。
什么?
今天下午,行政那边找人来给办公室搞消毒,说是为‘优化办公环境’。结果那帮人拿着喷雾器一通乱喷,把好几个同事的键盘都给喷坏了,你说逗不逗?
我的心猛地一沉。
消毒?
喷雾器?
我突然想起一件事。
那几台测试服务器,我为了方便调试,在机柜后面接了一个小型的无线AP,没走公司的有线网络。
那个AP,为了信号好,我把它藏在了……
我猛地回头,看向墙角那盆巨大的天堂鸟。
我离开的时候太匆忙,只顾着搬那些我亲手养大的植物。
这盆天堂鸟是公司本来就有的,我没怎么管过,所以也没想起来。
那个小小的、黑色的无线AP,就被我用扎带,绑在了天堂鸟最粗壮的茎干上,藏在茂密的叶子后面。
消毒水的喷雾,带着腐蚀性的化学成分,如果直接喷在上面……
AP短路,信号中断。
而测试服务器集群,为了节省成本,用的是最廉价的NAS存储,走的无线连接。
网络一断,存储读写自然就卡死了。
我靠。
我千算万算,没算到行政那帮蠢货会来这么一出。
这下好了,新账旧账,都得算我头上了。
李未?李未?还在吗?大飞在电话那头喊。
在,在。我回过神来,可能就是巧合吧。
也许吧。行了,不跟你说了,我还得继续加班呢。有空出来喝酒。
好。
挂了电话,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,后背有点发凉。
事情的走向,似乎开始偏离我的剧本了。
我设计的蓝屏大戏,本来是一场精准的外科手术式打击。
现在,却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消毒,变成了一场混乱的无差别攻击。
我看了看时间。
晚上九点。
距离48小时的最终时限,还剩下不到12个小时。
明天一早。
当所有人走进办公室,按下电脑开机键的时候……
那将是怎样一幅壮观的景象啊。
我既害怕,又期待。
第二天早上,我醒得格外早。
天还没亮,窗外只有几声零星的鸟叫。
我的心跳得很快,像是揣着一只兔子。
我没有看手机。
我害怕看到小刘的夺命连环call,也害怕看到任何来自公司的消息。
我就那么静静地坐着,听着时钟的滴答声。
八点。
九点。
九点半。
手机终于像疯了一样震动起来。
屏幕上,是小刘的名字。
我深吸一口气,按下了接听键。
电话那头不是小刘的声音,而是一阵嘈杂的、混乱的背景音。
有人在喊,有人在骂,还有键盘被砸在桌子上的声音。
喂?小刘?
未……未哥……小刘的声音抖得像筛糠,出事了……出大事了!
怎么了?慢慢说。我假装平静。
全……全都蓝了!他几乎是在嘶吼,公司里所有的电脑,所有的!开机就是蓝屏!服务器也连不上了!全都瘫了!
来了。
终于来了。
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,血液冲上头顶。
我几乎能想象出那幅画面:
几百台显示器,发出幽蓝色的、死亡一般的光,映照着一张张惊慌失措的脸。
王经理呢?他怎么说?我问。
他……他刚才一脚把机房的门踹开了,现在正在里面砸东西!他吼着说要报警抓你!
抓我?凭什么?
他说一定是你干的!他说你昨天搬走那些花,就是为了报复!
web云服务器
呵,他有证据吗?
我不知道啊未哥!现在怎么办啊!CTO也来了,脸黑得跟锅底一样!公司要完蛋了啊!
小刘真的快哭了。
我沉默了。
我是在报复吗?
是的。
但我的报复,本该是一场悄无声息的、充满技术美感的行为艺术。
我只是拔掉了维生系统。
是他们自己,让病人死掉的。
小刘,你别慌。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可靠,你听我说,你现在立刻离开机房,离王经理远一点。他现在在气头上,别让他把你当出气筒。
可是……
别可是了!这不是你能解决的问题。他们找不到原因的。你现在唯一要做的,就是保护好自己。
那……那你呢?未哥,这事真的跟你没关系吗?他还是问出了口。
我叹了口气。
小刘,从我签下离职协议那一刻起,这家公司的一切,就都跟我没关系了。
我挂了电话。
屋子里一片寂静。
窗外的太阳已经升起,金色的光芒照亮了我的植物园。
绿色的叶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生机勃勃。
而几十公里外的那个写字楼里,却是一片死寂的蓝色。
我打开电脑,登录了几个IT论坛和社交平台。
很快,我就看到了相关的帖子。
惊爆!国内某知名互联网公司遭遇黑客攻击,全公司系统瘫痪!
有内部员工透露,今早所有人都无法工作,疑似被勒索病毒入侵。
笑死,听说是因为开除了一个扫地僧级别的运维大佬。
凌梦云服务器
下面的评论五花八门。
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,有分析技术原因的,还有自称是该公司员工、出来现身说法的。
是真的!我们公司!现在全乱套了!听说IT部门的人都快疯了!
何止是疯了,我们老大当场就把手机给摔了。
我只想知道,今天还用不用上班?是不是可以带薪休假了?
我看着这些评论,嘴角忍不住上扬。
一种巨大的、病态的满足感,充满了我的内心。
你们裁掉我的时候,不就是觉得我无足轻重吗?
现在,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,你们错了。
错得离谱。
中午,我叫了披萨和炸鸡,还开了一瓶啤酒。
我举起酒杯,对着满屋子的植物。
敬你们。我说,我的战友们。
下午,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。
我看着那串数字,心脏漏跳了一拍。
我有一种预感。
我接起电话。
喂,是李未吗?
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沉稳,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。
我听出来了,这是公司CTO,赵总的声音。
一个我只在全体大会上,远远见过几次的大人物。
是我。
我是赵启明。他自报家门,公司现在的情况,我想你应该听说了。
略有耳闻。我喝了口啤酒,故意发出声音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李未,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这件事,是不是你做的?
赵总,您这是在质问我,还是在给我定罪?我反问。
我只是在陈述一个可能性。昨天,你被公司辞退。今天,公司整个系统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崩溃。这两件事,很难不让人联系到一起。
这叫‘有罪推定’。没有任何证据,就凭时间上的巧合,就把锅扣在我一个前员工头上。贵公司的企业文化,还真是……一脉相承啊。我的话里带着刺。
赵启明似乎被我噎了一下。
好,我们不谈这个。他很快调整了策略,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技术难题。外部请来的安全专家,查了一上午,毫无头绪。他们认为,这不像是外部攻击,更像是一种……内部的锁定机制。
他果然是技术出身,一针见血。
所以呢?
小刘……就是你带的那个实习生,他提到,你平时喜欢搞一些‘非官方’的个人项目。他还说,你昨天,搬走了办公室里所有的植物。
我的心跳开始加速。
赵总,您到底想说什么?
我想请你回来一趟。他的语气,从质问,变成了一种……请求。
以什么身份?犯罪嫌疑人吗?
不。他深吸一口气,仿佛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,以技术顾问的身份。我们聘请你,来解决这次危机。条件你开。
条件我开。
这四个字,像一颗炸弹,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响。
我等了七年,不就是在等这句话吗?
我本可以一口答应,然后狠狠地敲他们一笔。
但我没有。
愤怒和屈辱过后,一种更深层次的疲惫感涌了上来。
我为什么要回去?
回到那个冰冷的、没有人情味的地方?
去拯救那些曾经轻视我、抛弃我的人?
赵总,我缓缓开口,不好意思,我今天约了人,要去逛花鸟市场。
李未!他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,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!公司每瘫痪一个小时,损失都是数以百万计!这关系到几千人的饭碗!
他又开始拿大义来压我。
当初你们裁掉我的时候,怎么没想过这也关系到我的饭碗?我冷笑。
那……那是HR部门和业务部门的决定!我承认,这件事处理得非常草率!我代表公司,向你道歉!
道歉?
真廉价啊。
如果道歉有用的话,还要警察干什么?我把电影台词搬了出来。
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死寂。
我能想象到,赵启明此刻的脸色,一定比那些蓝屏还要难看。
李未,他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,你到底想要什么?
我想要什么?
我看着窗外,夕阳正一点点沉入地平线。
我想要王经理,亲自打电话给我,请我回去。我说。
还有,我要你们在公司内部,发全员通告,为辞退我的决定,向我公开道歉。
最后,这次的技术顾问费,我要这个数。
我报了一个足以让他在北京买一个厕所的数字。
你……赵启明倒吸一口凉气,你这是敲诈!
随你怎么说。你们可以继续请你们的外部专家,看看他们什么时候能找到那些藏在花盆里的树莓派。哦,对了,提醒他们一下,别忘了查查行政部那盆天堂鸟。
说完,我直接挂了电话。
世界清静了。
我靠在沙发上,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。
这不像是一场胜利,更像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。
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答应。
但这是我的底线。
尊严,有时候比钱更重要。
我拿起手机,给小刘发了条微信。
把天堂鸟下面的那个黑色小盒子,拔掉电源,重启一下试试。
这是我最后的善意。
至于其他的,就让他们自己头疼去吧。
一个小时后,王经理的电话打了过来。
他的声音,和我记忆中那个颐指气使的领导,判若两人。
那是一种混杂着屈辱、恐惧和一丝谄媚的、极其扭曲的声线。
喂……是……是李未吗?我是王强。
他甚至报出了自己的本名,而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王经理。
有事?我的声音冷得像冰。
那个……李未……之前的事,是我不对,是我有眼不识泰山,我……我给你赔不是了。
他在电话里,几乎是在哀求。
公司现在……真的顶不住了。赵总……赵总让我请你回来一趟,无论如何,帮帮忙。
你的意思是,求我?我故意问。
电话那头,我能听到他粗重的喘息声,和咬牙切齿的声音。
过了好几秒,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。
……是。
行啊。我说,车派到我楼下,我现在就过去。
另外,那份全员道歉信,我到公司的时候,要看到它出现在所有人的邮箱里。
好,好,没问题!他答应得比谁都快。
挂了电话,我站起身,走到镜子前。
镜子里的我,眼圈发黑,胡子拉碴,但眼神却异常明亮。
像一头蛰伏已久的野兽,终于等到了出击的时刻。
我没有换衣服,就穿着这身皱巴巴的T恤和牛仔裤。
我要让他们看到,他们抛弃的,到底是怎样一个不修边幅的家伙。
我从我的植物园里,挑了一盆最小的、也是最关键的。
就是那盆琴叶榕。
我抱着它,就像抱着我的权杖。
楼下,一辆黑色的奥迪A6已经停在那里。
司机看到我,立刻下车,恭敬地为我打开车门。
这待遇,我在这家公司七年,从未享受过。
真是讽刺。
车子平稳地驶向那个我无比熟悉的写字楼。
一路上,我一言不发,只是静静地看着怀里的琴叶榕。
它的叶片,在昏暗的车厢里,泛着墨绿色的光。
就是这个小东西,和它的七个兄弟,用沉默的方式,颠覆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。
抵达公司楼下时,我看到了壮观的一幕。
王经理,还有HR总监雪莉姐,居然亲自站在大门口等我。
旁边,还站着几个我不认识的高管模样的人。
看到我下车,王经理立刻堆起满脸的笑,迎了上来。
李未,你可算来了!快,快请进!
他的腰弯得像一只煮熟的虾。
雪莉姐的表情更是精彩,那张习惯了假笑的脸,此刻僵硬得像戴了一张面具,想笑,又笑不出来。
我没理他们,抱着我的琴叶-榕,径直走向电梯。
他们赶紧跟在后面,像一群随从。
电梯里,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。
那个……道歉信,已经发了。雪莉姐小声说,像在汇报工作。
哦。我应了一声,眼睛都没斜一下。
叮。
电梯门打开。
熟悉的办公区,此刻却是一片死寂。
所有人都没在工作,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,窃窃私语。
看到我出现,所有人的目光,瞬间聚焦在我身上。
那眼神,混杂着敬畏、好奇,还有一丝恐惧。
我仿佛不是一个前员工,而是一个手握核弹按钮的独裁者。
我抱着花盆,穿过人群,走向那个曾经属于我的角落。
小刘看到我,眼睛都红了,像看到了救星。
未哥!
我朝他点了点头。
我没有直接走向机房。
我把琴叶榕,轻轻地放回了它原来的位置——那个靠窗的角落。
然后,我从背包里,拿出了另外七个用胶带缠好的树莓派。
我当着所有人的面,一个一个地,把它们重新塞回了那些空荡荡的花盆底下。
金钱树。
龟背竹。
和平百合。
……
我每放好一个,周围的空气就仿佛凝重一分。
所有人都屏住呼吸,看着我这诡异而庄重的仪式。
他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,这些廉价的微型电脑,和他们数以亿计的生意之间,到底有什么神秘的联系。
最后,我走到了王经理的办公室门口。
他的办公室里,也有一盆我养的植物。
一盆高大的,散尾葵。
我走进去,王经理赶紧从椅子上弹起来,给我让座。
我没坐,径直走到散尾葵旁边,把最后一个树莓派,也安放好了。
做完这一切,我拍了拍手上的灰。
好了。我说。
王经理和跟进来的赵总,都一脸茫然地看着我。
好了?这就好了?赵总难以置信地问。
等几分钟。我说,让它们……互相认识一下。
我走到办公区中央,找了张空椅子坐下。
我翘起二郎腿,好整以暇地看着周围。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
一分钟。
两分钟。
三分钟。
突然,办公区的一个角落里,传来一声惊喜的尖叫。
我的电脑!我的电脑好了!
紧接着,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响了起来。
我的也好了!
能登录了!!
蓝屏消失了!恢复正常了!
那些幽蓝色的屏幕,像被施了魔法一样,一个接一个地,切换回了熟悉的Windows桌面。
整个办公室,瞬间从地狱变成了天堂。
人们欢呼着,拥抱着,像劫后余生。
只有我,静静地坐在那里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赵总和王经理,快步走到一台电脑前,亲眼确认了系统恢复正常。
赵总转过身,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我。
你是怎么做到的?
我站起身,走到他面前。
赵总,一个好的系统架构,不仅要考虑软件,还要考虑人性。
我不相信任何写在纸上的管理规定,我只相信代码。
我设计的‘绿盾’系统,本质上,是一个‘员工-公司’之间的信任协议。这些植物,就是协议的载官。当你们单方面撕毁协议,辞退我的时候,也就意味着,你们主动拔掉了这些‘信任’的根。
系统崩溃,不是因为我的报复。而是因为你们的背信弃义,触发了它自己的保护机制。
我的声音不大,但足以让周围的高管们都听清楚。
他们的脸上,青一阵,白一阵。
至于技术细节,我笑了笑,我想,这应该属于我这次‘顾问服务’的商业机密吧?
赵总沉默了。
他是个聪明人,他知道我不会告诉他核心秘密。
即使告诉他,他也未必能懂。
那是我用七年的时间和无数个不眠之夜,构建起来的,独属于我的王国。
你赢了。他终于开口,声音里充满了挫败感。
我没想过要赢。我说,我只是不想输得那么难看。
你提的条件,公司都答应。顾问费,明天就会打到你的账上。赵总说,另外,我正式邀请你,重新回到公司,担任技术总监的职位,直接向我汇报。
技术总监。
这真是一个诱人的职位。
薪水,权力,地位,全都有了。
我只要点点头,就能完成一次华丽的逆袭。
从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失败者,变成一个衣锦还乡的英雄。
所有同事,都用一种期待的眼神看着我。
小刘更是激动得满脸通红。
我看着赵总,看着王经理那张谄媚的脸,看着雪莉姐那副比哭还难看的假笑。
我又看了看那些刚刚复活的植物。
它们在各自的角落里,静静地待着,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我想起我那个被它们挤得满满当-当的出租屋。
那个小小的,却充满了生机和自由的热带雨林。
我突然觉得,这个宽敞明亮、四季恒温的办公室,像一个巨大的、华丽的笼子。
我笑了。
赵总,谢谢你的好意。
但是我拒绝。
所有人都愣住了。
为什么?赵总不解地问,我们给出的条件,已经是业内顶级的了。
我走到那盆琴叶榕旁边,轻轻抚摸着它的一片叶子。
有些植物,一旦被从不适合它的土壤里移出来,就再也不想被栽回去了。
哪怕新的花盆再名贵,土壤再肥沃。
因为它已经尝过……自由的滋味了。
我说完,没再看任何人的表情,转身就走。
这一次,没有人敢拦我。
我身后,是死一般的寂静。
我走进电梯,按下一楼。
电梯门缓缓关上,隔绝了外面那个复杂的世界。
在门关上的最后一刻,我看到了小刘追出来的身影,他张着嘴,似乎想说什么,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。
我朝他挥了挥手。
走出写字楼,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眼睛有点疼。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空气里,有汽车的尾气,有路边小吃的香味,还有风带来的、不知名的花香。
这是人间的味道。
真实,而自由。
第二天,我的银行账户里,多了一长串的零。
我没有去挥霍,也没有立刻开始新的生活。
我花了一天的时间,把我那个小小的出租屋,彻底改造成了一个真正的植物园。
我买了新的花架,买了专业的补光灯,买了各种各样的营养液。
我把每一盆植物,都安排在了最适合它们的位置。
阳光、水分、空气,一切都恰到好处。
一周后,我用那笔顾问费,注册了-我自己的公司。
名字很简单,就叫绿盾网络安全工作室。
办公室,就是我的出租屋。
员工,除了我,就是这满屋子的植物。
我的第一个客户,是大飞介绍的。
一家初创公司,被竞争对手搞得焦头烂额,需要一套稳定又不走寻常路的安全系统。
我和他们的CEO,就在我的植物园里,喝着茶,聊完了整个方案。
他看着我那些长势喜人的植物,又看了看我那台连接着无数传感器的电脑,眼神里充满了好奇和信任。
李先生,他最后说,你让我相信,技术,真的是有生命的。
我笑了。
是的,有生命。
而且,有脾气。
后来,我的生意越做越好。
很多客户慕名而来,他们不只看重我的技术,更欣赏我那套万物皆可为探针的奇特哲学。
我再也没有回过那家公司。
只是偶尔会从大飞或者小刘的口中,听到一些零星的消息。
据说,王经理因为这次事件,被直接开除了,走的时候比我还不体面。
据说,雪莉姐也被降了职,风光不再。
据说,公司花了重金,请了一个新的技术团队,想要复制我的绿盾系统,但搞了半年,连皮毛都没摸到。
他们永远也不会明白。
那个系统的核心,不是代码,也不是那些树莓派。
而是我。
是我在那七年里,日复一日,对每一台服务器、每一段网络、甚至每一盆植物的熟悉和掌控。
是我这个人,才是那个系统真正的、无法被替换的根。
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,我正在给我的龟背竹擦拭叶片。
手机响了,是一个新的客户。
我夹着手机,一边和对方交谈,一边拿起喷壶,给文竹纤细的叶子,喷上细密的水雾。
水珠在阳光下,折射出彩虹一样的光。
我的身后,那十六盆曾经陪我离家出走的植物,和后来加入的几十个新成员,构成了一片繁盛而宁静的绿色世界。
它们是我的伙伴,我的卫兵,也是我的勋章。
它们和我一起,在这座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,扎下了新的根。
并且,自由地,野蛮地,生长着。
云盘服务器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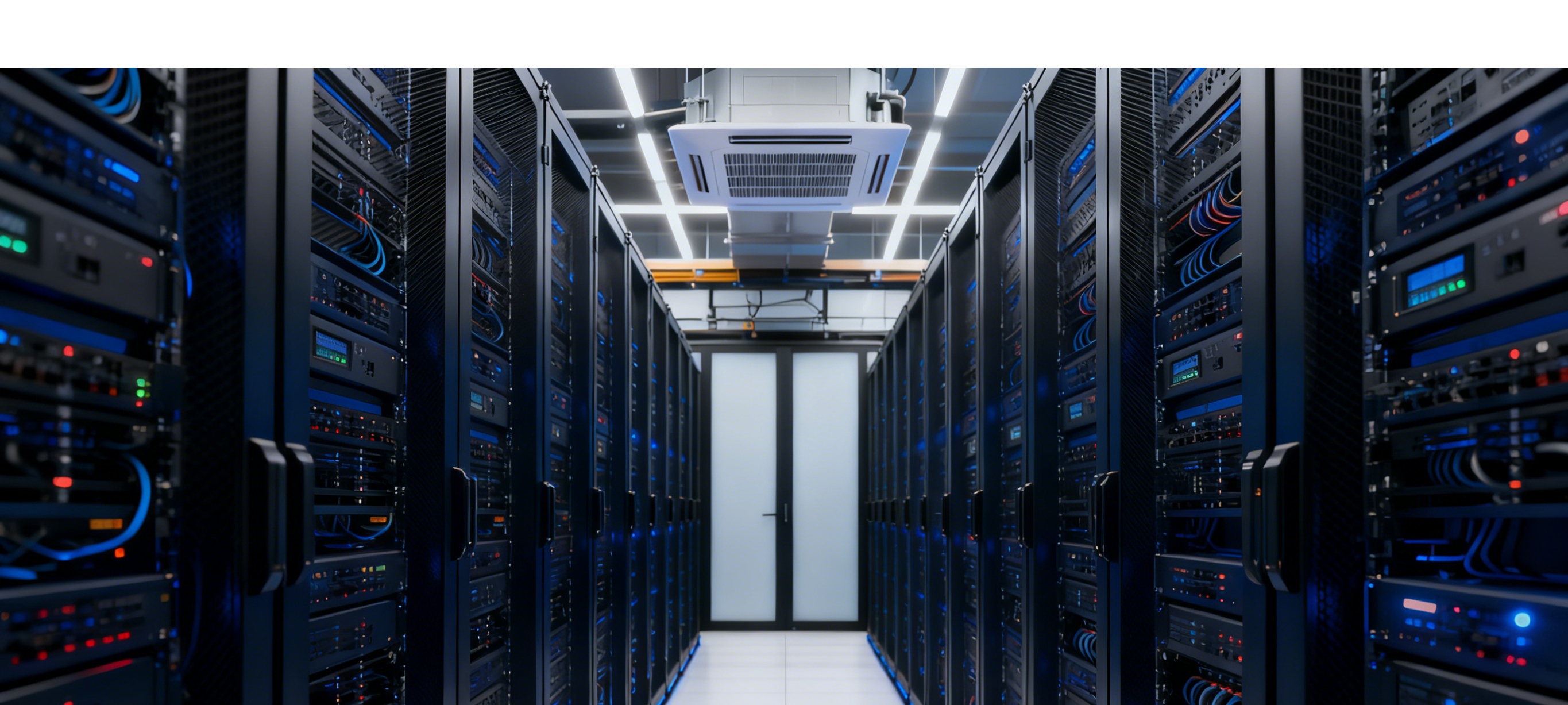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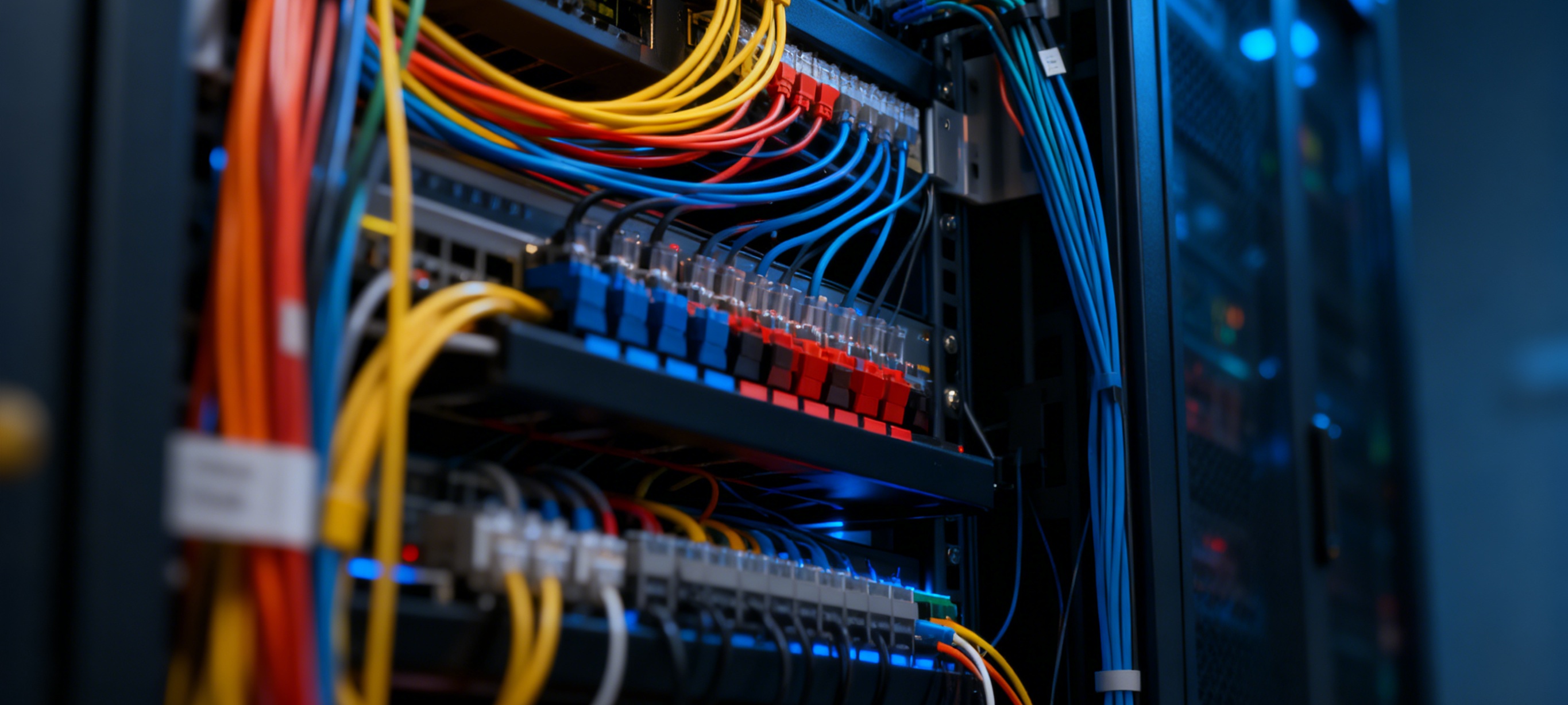
扫码关注
微信好友
关注抖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