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时收费云服务器74年,我把返城指标让给女友,她走后,就再也没了音讯
国内云服务器价格

火车开动的时候,汽笛声又长又尖,像一把生锈的刀子,狠狠地豁开了东北荒原的天。
林婉的脸贴在冰冷的车窗上,已经哭成了一团模糊的影子。
她的嘴在动,我听不见,但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。
智云服务器
等我,陈劲,一定等我。
我站在月台上,没动,也没哭。
北风卷着煤灰,吹得我睁不开眼。
我只是死死地盯着那节车厢,直到它变成一个小黑点,最后被地平线彻底吞掉。
那一年,是1974年。
我二十二岁,把唯一的返城指标,给了我的女朋友林婉。
我以为,我给出去的是一张车票,一个希望。
我以为,她回去的那个地方,叫上海,也叫我们的未来。
后来我才知道,我给出去的,是我这辈子剩下的所有日子。
而她回去的那个地方,叫永别。
回到红星公社七分队的集体宿舍,天已经黑透了。
土炕冰凉,像死人。
我没烧火,就那么和衣躺了上去。
屋子里空荡荡的,另一半土炕上,林婉的铺盖已经卷走了,只留下一个浅浅的人形印子,好像她从来没在这里睡过一样。
可空气里,到处都是她的味道。
是那种廉价雪花膏混着她头发的香味。
我把头埋在我的枕头里,那上面也有。
我猛地坐起来,感觉喘不过气。
脑子里全是她临走前一晚说的话。
陈劲,你相信我吗?
她攥着我的手,眼睛在煤油灯下亮得像两颗星星。
我说,信。
我不信你,我还能信谁?
这个指标对我太重要了,你知道的,我爸妈……他们需要我。
我知道。
她父亲是大学教授,母亲是医生,在那几年,这种身份就是原罪。她不止一次在夜里哭醒,说梦见他们被人批斗。
而我呢?
我爹是轧钢厂的普通工人,我妈没工作,家里还有两个弟弟。我回去,无非就是从一个坑跳进另一个坑,从挣工分变成在厂里当学徒。
她说:你让我先回去,我安顿好了,马上就想办法,把你也弄回去。我爸有很多学生,现在都慢慢恢复工作了,肯定有办法的。
最多一年,不,半年!半年我就接你回去!
我们回上海,就结婚。
她一句一句地说,像是在描画一幅全世界最美的画。
画上有我们的小家,有热气腾腾的饭菜,有不必再挨饿受冻的冬天。
我看着她的眼睛,点了头。
其实,那个指标下来的时候,分队书记第一个找的是我。
我这几年在队里,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,年底工分年年最高。我是公认的老实人,也是公认的傻力气。
书记拍着我的肩膀说:小陈,你小子熬出头了。回城吧,别在这土里刨一辈子了。
我当时激动得手都在抖。
回城,回上海。
这两个字,像两道惊雷,在我脑子里炸开。
我终于可以离开这片黑土地了,离开这无休无止的农活,离开这能把人骨头都冻酥的冬天。
我第一个告诉了林婉。
我冲进她的宿舍,抱起她转了好几个圈。
我以为她会跟我一样高兴。
但她没有。
她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,然后就哭了。
不是高兴的哭,是那种委屈的,绝望的哭。
她抱着我,哭得浑身发抖。
陈劲,我怎么办?我怎么办?
那一刻,我心里的所有狂喜,瞬间就被浇灭了。
是啊,我走了,她怎么办?
她身体不好,干不了重活,工分总是挣得最少的那个。冬天她总是生病,咳个不停,全靠我把自己的口粮匀给她,才勉强熬过来。
我走了,谁来照顾她?
那天晚上,我们俩坐在土炕上,一夜没说话。
煤油灯的火苗,跳了一下,又一下。
最后,是我先开的口。
我说:婉儿,你回去吧。
她猛地抬起头,眼睛里全是泪,还有一丝不敢相信。
我说:你比我更需要这个指标。你家里的情况,比我更难。
她没说话,只是咬着嘴唇,眼泪流得更凶了。
我身体好,我能扛。你不行。
你先回去,安顿好了,再想办法接我。我相信你。
我把她说的那些话,又对着她说了一遍。
好像这么一说,就不是我把未来让给了她,而是我们共同投资了一个未来,她只是先去探路的那个人。
她扑进我怀里,哭得像个孩子。
陈劲,你真好。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的人。
我发誓,我这辈子,非你不嫁。
我到了上海,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信,每天一封!
现在,我躺在这冰冷的土炕上,耳边还回响着她的誓言。
可心里,却空得像被北风反复穿过的旷野。
第二天,我照常出工。
分队长看见我,挺意外。
哟,陈劲,没走啊?我还以为你小子今天就坐火车回上海享福去了。
队里几个相熟的知青也围过来。
劲哥,不够意思啊,要回城了也不说一声?
就是,得请客啊!
我把铁锹往地上一插,闷声说:我不回去了。
所有人都愣住了。
分队长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:你说啥?
我说,我不回去了。我重复了一遍,那个指标,我让给林婉了。
空气瞬间安静了。
所有人的眼神都变得很奇怪,像在看一个疯子。
和我一个宿舍的赵磊,一把将我拉到田埂边上。
陈劲,你他妈是不是疯了?!他压低了声音吼,那是返城指标!能回上海!你知不知道多少人挤破了头都拿不到?你就这么让了?
我说:她比我更需要。
需要个屁!赵磊气得脸都红了,她需要,你就得让?你们俩还没结婚呢!你凭什么啊?再说了,她跟你保证了什么?她回去了,人生地不熟的,她自己都站不稳,拿什么给你办?你这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!
她会给我写信的。我有点底气不足。
写信?写信能让你回城?赵磊冷笑一声,陈劲,我跟你说句不好听的。人心隔肚皮。这年头,亲兄弟还为了一口吃的打破头呢,你把命根子都给了她,你等着吧,有你后悔的那天。
我没说话。
因为我心里也怕。
我怕赵磊说的,都是真的。
但我不敢想。
我只能拼命地干活,把所有力气都花在刨地、翻土上。
只有累到连手指头都动不了的时候,我才不会去想,林婉现在在做什么。
她是不是已经到家了?
她是不是正在给她爸妈讲我们在乡下的事?
她是不是,已经坐下来,开始给我写第一封信了?
我开始等信。
每天收工后,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村口的代销点。
那是我们公社唯一能收发信件的地方。
代销点的王大婶,每次看见我都笑。
小陈,等对象信呢?
我红着脸点点头。
一天,两天,一个星期。
没有。
王大婶安慰我:别急,信从上海到咱们这嘎达,慢得很。
我也这么安慰自己。
路太远了,邮递员走路得走好几天。
半个月。
还是没有。
赵磊看我的眼神,已经从愤怒变成了同情。
他不再骂我了,只是偶尔叹口气,拍拍我的肩膀。
一个月过去了。
一封信都没有。
我开始慌了。
每天晚上,我都睡不着。
土炕的另一边,那个浅浅的人形印子,好像在无声地嘲笑我。
我开始胡思乱想。
她是不是出事了?
火车上遇到坏人了?还是回家路上出了什么意外?
或者,她家里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糟,她一回去就焦头烂额,根本没时间写信?
我不敢往最坏的方向想。
我不敢想,她是不是忘了我。
不,不可能。
林婉不是那样的人。
她那么爱我,她走的时候哭得那么伤心,她还发了誓。
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
第二个月,我终于坐不住了。
我跟分队长请了假,说家里有急事,然后揣上我攒了半年的十几块钱,扒上了一辆拉煤的货车,一路颠簸到了县城。
我直奔邮电局。
我想给她拍个电报。
我记得她家的地址,上海市,虹口区,长春路xx弄xx号。
这个地址,我默念过无数遍,已经刻在了骨子里。
我趴在柜台上,一个字一个字地填写电报单。
林婉,见电速回,万分想念,陈劲。
每一个字,都像千斤重。
电报员是个面无表情的中年女人,她扫了一眼地址,又扫了我一眼。
字数超了,按规矩要加钱。
加。我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,摊在柜台上。
她数了数,把钱收了进去,盖了戳。
好了。
我站在那,没动。
还有事?她不耐烦地问。
同志,这个……这个电报,大概多久能到?
快的话三四天,慢的话一个礼拜。
我千恩万谢地走了。
回到公社,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等待。
这次,我等的是回电。
我觉得,电报这么紧急的东西,她看到了,一定会马上回复的。
我又等了半个月。
还是什么都没有。
去代销点问信,王大婶看我的眼神,也从打趣变成了怜悯。
小陈啊,要不……你再拍个电报问问?
我没钱了。
我连买一包最便宜的大丰收香烟的钱都没有了。
赵磊看不下去了,塞给我五块钱。
去,再去问问。这次问清楚点,是不是家里出事了。
我又去了一趟县城。
这次,电报的内容是:家中是否平安?见电速回。
我把所有的希望,都寄托在了这封电报上。
如果她家出事了,她不回信,情有可原。
只要人平安就好。
然而,这封电-报,也像泥牛入海。
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。
秋天来了,高粱红了,玉米熟了。
队里开始抢收,忙得人脚不沾地。
我像一头牲口一样干活,白天累到虚脱,晚上倒头就睡。
我不敢让自己闲下来。
我怕一闲下来,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,就会把我活活吞掉。
队里的知青们,看我的眼神也变了。
再也没有人拿我和林婉的事开玩笑。
他们只是默默地,有时候会把自己的窝窝头分我半个。
我知道,在他们眼里,我陈劲,已经成了一个笑话。
一个为了女人,把自己前途搭进去的,彻头彻尾的傻子。
1974年的冬天,来得特别早,也特别冷。
大雪封山,我们窝在宿舍里,无所事事。
唯一的娱乐,就是听广播,或者聚在一起吹牛。
那天,赵磊不知道从哪儿弄来半瓶烧刀子。
他把我拉到角落,给我倒了一满杯。
陈劲,喝点吧,暖暖身子。
我接过来,一口就闷了。
辛辣的酒液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,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。
赵磊又给我倒上。
想开点。他说,天底下的女人多的是,不值当。
我没说话,又是一口。
几杯酒下肚,我感觉脑子开始发昏,心里堵了几个月的东西,也开始往上涌。
赵磊,你说……她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?我的声音在抖。
赵磊沉默了一会儿。
陈劲,咱们是兄弟,我跟你说句实话。
嗯。
你别等了。
……
她要是心里有你,一封信,一张邮票,几分钱的事,她会不给你寄?都快半年了,她连个屁都没放一个。这说明什么?
赵-磊把酒杯重重地放在桌上。
说明人家到了大上海,把你这个乡下的土包子,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!
她不是那样的人!我吼了一声,声音却虚得像漏了风。
是不是那样的人,你自己心里没数吗?赵磊指着我的鼻子,你就是不肯承认!你就是自欺欺人!
我一把推开他,冲出了宿舍。
外面的雪下得正大,像要把整个世界都埋起来。
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外跑,不知道要去哪儿。
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,但我感觉不到疼。
心里的疼,比这疼一万倍。
我跑到我们以前经常约会的那个小山坡上。
夏天的时候,我们俩会躺在这里的草地上,看天上的云。
她会指着云,说,那朵像兔子,那朵像小狗。
她会把头枕在我的胳膊上,说,陈劲,等我们回了上海,我就带你去吃最好吃的生煎包,带你去逛南京路。
她说,上海的冬天,是不会下这么大的雪的。
现在,我一个人站在这雪地里,感觉自己就像个被全世界遗忘的雪人,马上就要冻僵了。
我终于忍不住,蹲在地上,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。
哭声被风雪一吹,就散了,什么都听不见。
从那天起,我再也没去代销点问过信。
我把林婉这个名字,连同那段记忆,一起埋在了心底最深的地方。
我像个行尸走肉一样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
日子过得没有一点盼头。
时间一晃,就是三年。
1977年,恢复高考的消息,像春雷一样,炸响了整个知青点。
所有人都疯了。
大家开始到处找书,找复习资料。
宿舍里,晚上灯火通明,所有人都在埋头苦读。
只有我,无动于衷。
赵磊拿着一本皱巴巴的数学手册,跑来劝我。
陈劲,你也试试!这是咱们唯一的机会了!
我摇摇头。
我早忘光了。
忘光了可以再学啊!你高中的时候成绩不是挺好的吗?比我强多了!
我还是摇头。
我的心,早就在三年前那个冬天,冻死了。
什么高考,什么返城,对我来说,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
赵磊恨铁不成钢地走了。
后来,他真的考上了。
是北京的一所大学。
走的那天,很多知青都去送他。
他也像当年的林婉一样,坐上了离开这里的火车。
临走前,他找到我。
他塞给我一个地址。
陈劲,这是林婉家的地址。我托北京的亲戚,费了好大劲才打听到的。她家早就搬了,这是新地址。
我看着纸条上的那行字,手有点抖。
你……打听这个干什么?
赵磊叹了口气:我就是不甘心。我就是想知道,那个女人,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
他顿了顿,又说:陈劲,我知道你心里还有疙瘩。等我到了北京,安顿下来,我帮你去上海问问。不管结果怎么样,你总得知道个真相,对自己有个交代。
我捏着那张纸条,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
赵磊走了。
知青点的人,陆陆续-续都走了。
有的考上了大学,有的通过各种关系,办了病退、困退。
最后,偌大的一个知青点,只剩下我,还有其他几个回不去的人。
我们被安排着,继续在队里干活。
日子又恢复了那种死水般的平静。
我没有给赵磊写信,也没有去打听林婉的任何消息。
我怕。
我怕知道那个我不敢想象的真相。
就这么又过了两年。
1979年,知青大返城的浪潮终于来了。
我也终于拿到了那张迟到了五年的,回上海的火车票。
当我拎着一个破旧的网兜,站在上海火车站的站台上时,我感觉像做梦一样。
空气里是熟悉的,带着煤烟味的潮湿气息。
耳边是听了无数遍的,软糯的上海话。
我回来了。
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
这里的一切,都让我感到陌生和疏远。
我先回了家。
五年没见,我爸妈都老了。
我爸背驼了,头发也白了大半。我妈的眼睛,因为常年糊火柴盒,已经看不太清东西了。
两个弟弟也长大了,都进了工厂,也都有了对象。
二十几平米的亭子间里,挤着一家五口人,转身都困难。
我的回来,并没有给这个家带来多少喜悦,反而增添了负担。
我没有工作,没有户口,成了一个黑人。
我爸托了厂里的老关系,想把我弄进去当个临时工。
跑了好几个月,送了无数条烟,说了无数句好话,最后还是没成。
那段时间,我每天都在街上闲逛。
上海的街道,和我记忆里的一样,又不一样。
梧桐树还是那些梧桐树,但房子好像都变旧了,人也变得更匆忙了。
我好几次,都走到了长春路。
那是林婉以前住的地方。
但我从来没有拐进那条弄堂。
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
直到有一天,我在街上碰到了赵磊。
他大学毕业,分配到了上海的一家研究所,穿着一身笔挺的干部服,戴着眼镜,文质彬彬。
我们俩在淮海路的街角偶遇,看着对方,都愣了半天。
最后,还是他先开了口。
陈劲?
赵磊?
我们找了个小饭馆,要了两瓶啤酒,几碟小菜。
他问我这几年的情况。
我一五一十地说了。
他听完,沉默了很久。
陈劲,你受苦了。
我摇摇头,喝了一大口啤酒。
都过去了。
他看着我,犹豫了一下,说:那件事……你想知道吗?
我的心,猛地揪了一下。
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。
我没说话,只是看着他。
赵磊叹了口气:我帮你打听了。
我刚到北京那会儿,就按那个新地址,给她写了封信。没回。
后来,我托我上海的舅舅,去那个地址找过。她家确实住那儿。但我舅舅去了好几次,都没碰到她。她家里人说,她不在。
再后来……我毕业分配到上海,我自己去找过。
赵磊端起酒杯,一口喝干。
我见到她了。
我的呼吸,瞬间停止了。
她……她怎么样?我艰难地问出口。
她结婚了。
国内十大云服务器
赵磊看着我的眼睛,一字一句地说。
嫁给了一个当官的儿子。孩子都两岁了。
轰的一声。
我感觉我整个世界都炸了。
所有的侥f幸,所有的幻想,在这一刻,碎得连渣都不剩。
我坐在那,一动不动,像个木头人。
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赵磊说了很多话,骂林婉忘恩负义,骂她是个骗子,是个婊子。
我一句都没听进去。
我只记得他说:我问她,还记不记得东北有个叫陈劲的。你猜她怎么说?
我抬起头,眼睛发直。
她说,‘哦,记得。那时候年轻,不懂事。’
赵磊学着她的语气,轻描淡写。
‘我们早就不联系了。也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,我先生不喜欢。’
陈劲,我当时真想抽她!我真想告诉她,你为了她,在乡下多等了五年!你为了她,把自己一辈子都毁了!
可我没说。
赵磊的眼圈红了。
我觉得,不值当。跟那种女人,没什么好说的。
那天晚上,我喝得酩酊大醉。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。
第二天醒来,头痛欲裂。
我躺在我的小阁楼里,看着天花板上斑驳的霉点,心里一片死寂。
结束了。
那个我爱了那么多年,等了那么多年的女人,那个我以为会是我的未来的女人,就这样,用一句年轻不懂事,给我和她的过去,画上了一个句号。
一个无比潦草,又无比残忍的句号。
我没有哭。
眼泪,好像早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里,流干了。
我只是觉得,可笑。
太可笑了。
我陈劲,就是个天底下最大的傻子。
从那天起,我再也没有去想过林婉。
我开始拼命地找工作。
什么活我都干。
去码头扛过麻袋,去建筑队搬过砖,去菜市场帮人卖过菜。
只要能挣到钱,只要能让自己活下去。
我爸妈看我这样,心里难受,但也帮不上什么忙。
他们只能每天晚上,多给我留一碗饭。
后来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了。
个体户,这个词开始出现。
我用我几年攒下来的一点钱,在弄堂口,支了个摊子。
修自行车。
我手艺是跟队里的老乡学的,还不错。
一开始,生意不好。
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。
但我肯吃苦,收费也公道。
慢慢的,回头客多了起来。
我的小摊子,从一个,变成了两个。
再后来,我租下了一个小门面,开了个车行。
不光修车,也卖车。
生意越做越大。
到了九十年代,我已经成了我们那一片,小有名气的陈老板。
我买了房子,把爸妈接过来一起住。
也给两个弟弟都张罗着,买了婚房。
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
很多人给我介绍对象。
有老师,有护士,有工厂的女工。
我都见了,但最后,都没成。
不是人家看不上我,是我觉得,没意思。
我的心,好像缺了一块。
不管用什么,都填不满。
有时候夜深人静,我一个人坐在我的车行里,闻着机油和橡胶的味道,我会突然想起那个东北的小山坡。
想起那个枕在我胳膊上,给我讲上海有多好的女孩子。
我会想,如果当年,我没有把指标让给她,现在会是什么样?
也许,我会顺利地回到上海,进工厂当个工人。
然后,按部就班地结婚,生子。
过着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,平凡的日子。
我不会有现在的车行,不会有现在的钱。
但也许,我会比现在快乐。
可人生,没有如果。
我再也没见过林婉。
上海这么大,又这么小。
我有时候会想,也许我们曾经在某条马路上擦肩而过。
也许我们曾经在同一家商店里买过东西。
但我们,终究是没有再见过。
直到2010年。
那一年,我快六十岁了。
我的车行,已经交给了我的侄子打理。
我每天的生活,就是喝喝茶,看看报纸,或者去公园里跟老头们下下棋。
有一天,赵磊突然给我打电话。
他已经退休了,现在在一个老年大学里教书法。
老陈,出来喝一杯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怪。
我们约在了一家老饭店。
他看起来,比我还老,头发全白了。
我们俩喝着黄酒,聊着以前的事。
聊着聊着,他突然说:陈劲,我前两天,碰到林婉了。
我夹菜的筷子,顿了一下。
已经快四十年了。
这个名字,从别人口中说出来,还是像一根针,轻轻地扎了我一下。
不疼,但很清晰。
哦。我淡淡地应了一声,继续吃菜。
她……过得不好。赵磊说。
我没做声。
她男人,前几年因为贪污,进去了。判了无期。
家也被抄了。房子,钱,都没了。
她儿子,不养她。嫌她丢人。
她现在,一个人租在一个很小的阁楼里,靠给人家打零工过活。身体也不好,一身的病。
赵磊看着我,小心翼翼地。
她跟我打听你。她问我,你现在怎么样了。
我放下筷子,端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
你告诉她了?
赵磊点点头:我没忍住。我把你现在的情况,都跟她说了。我说你现在是大老板,过得比谁都好。
我笑了笑。
然后呢?她什么反应?
她哭了。赵磊说,她哭着说,她对不起你。她说,她当年,是有苦衷的。
苦衷?我冷笑一声。
她说,她当年一回到上海,她爸就被隔离审查了。家里全乱了。她一个女孩子,根本没办法。后来,是她现在这个男人家里,出了力,把她爸保了出来。但条件是,她必须嫁过去。
她说,她不是没想过反抗。但她看着她爸妈一夜白了头,她心软了。她说,她给你写过信,解释这一切。但信,都被她妈给烧了。她妈说,不能再拖累你了。
赵磊一口气说完,看着我。
我沉默了很久。
这个故事,听起来,合情合理。
甚至,有点感人。
一个为了家庭,牺牲自己爱情的,苦命的女人。
如果是在三十年前听到,我可能会信。
我甚至可能会原谅她。
但现在,我不会了。
赵磊,我看着他,很平静地说,你信吗?
赵磊愣住了。
我……
一句对不起,一句有苦衷,就把所有的背叛和伤害,都抹掉了?
那我呢?我那在乡下白白等死的五年,谁来赔我?
我那颗被伤透了的心,谁来补?
她有她的苦衷,难道我就没有我的绝望吗?
我一口气说完,感觉心里舒畅了很多。
堵了几十年的那口恶气,好像终于吐出来了。
赵磊没说话,只是给我把酒满上。
她……想见你一面。他说。
我摇摇头。
不见。
她说,她想当面跟你道个歉。
不需要。
我站起身。
赵磊,我先走了。这顿我请。
我把钱放在桌上,转身就走。
我没有回头。
我怕一回头,就会心软。
走出饭店,外面的天已经黑了。
华灯初上,车水马龙。
我一个人走在人行道上,感觉自己像个孤魂野鬼。
赵磊说的那些话,像电影一样,在我脑子里一遍遍地放。
她说她有苦衷。
她说她给我写过信。
是真的吗?
还是,只是她现在落魄了,想从我这里,得到一点同情和帮助?
我不知道。
我也不想知道了。
真相是什么,已经不重要了。
重要的是,我们的人生,早就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。
我们之间,隔着的,不是一句道歉,也不是一个拥抱。
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,那四十年。
过了几天,赵磊又来了。
他没给我打电话,直接找到了我家。
他看起来很憔悴。
老陈,我求你个事。
他从口袋里,掏出一个信封。
信封黄黄的,很旧了。
这是林婉托我转交给你的。
我没接。
她说,你看完这封信,如果还不想见她,她就再也不纠缠你了。
我看着那个信封,犹豫了。
最终,我还是接了过来。
赵磊走了。
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,看着手里的信,看了很久。
信封上没有贴邮票,也没有邮戳。
像是直接送过来的。
我把信拆开。
里面是几张信纸。
字迹娟秀,很熟悉。
是林婉的字。
陈劲,见字如面。
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,想了很久,还是觉得,叫你陈劲,最亲切。
赵磊应该都跟你说了。我的事,我的处境。我知道,我现在这个样子,再来找你,很可笑,也很无耻。
但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声,对不起。
我知道,这三个字,弥补不了什么。它太轻了,轻得像一片羽毛,而我欠你的,是一座山。
当年,我回到上海,家里确实出事了。我爸被抓了,我妈整天以泪洗面。我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,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通。那种绝望,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形容。
是,后来是王家(我前夫家)帮了我们。但代价,就是我的婚姻。
我挣扎过,我反抗过。我跟我妈说,我已经在东北有男朋友了,我非他不嫁。我妈打了我一巴掌,她说,陈劲能救你爸吗?他能让咱们家不家破人亡吗?
我哑口无言。
我给你写了信,写了很多封。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了。我求你忘了我,开始新的生活。但那些信,都被我妈烧了。她怕你冲动,跑到上海来找我,到时候,把你也给连累了。
她说,长痛不如短痛。既然给不了你未来,就断得干净一点。
所以,在你那里,我成了一个毫无音讯的,忘恩负义的骗子。
我知道,你不信。没关系。换做是我,我也不信。
我只是想告诉你,在我心里,从来没有忘记过你。在嫁人前的那个晚上,我哭了一夜。我想的,全都是你。我想起你在雪地里,把你的棉大衣脱下来给我穿。我想起你为了让我多吃一口饭,自己饿着肚子。我想起你把唯一的返城指标让给我时,说的那句,‘我相信你’。
陈劲,我这辈子,辜负了很多人。但我最对不起的,就是你。
我嫁人后,生活并不好。王家看不起我们家,我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。我过得,像个金丝雀,没有一点尊严。我好多次都想,如果当年,我们都没有回城,就那么在东北的那个小山坡上,过一辈子,会不会比现在幸福?
后来,他出事了。所有人都离我而去。我病了,穷了,老了。我才发现,我这一生,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过。
我唯一的念想,就是想再见你一面。不求你原谅,只想亲口跟你说一声,对不起。
如果你不想见我,没关系。我理解。
这张纸条上,是我的地址。如果你……想来看看我这个笑话,就来吧。
林婉。
信的最后,附着一张小纸条,上面写着一个地址。
在城市的另一端,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,破旧的老城区。
我把信,反复看了好几遍。
每一个字,都像一把小锤子,敲在我的心上。
我不知道该相信,还是不该相信。
我的理智告诉我,这都是她的借口。
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,编造出来的,博取同情的故事。
但我的情感,却有一丝动摇。
我想起了当年的林婉。
那个善良的,柔弱的,会因为一只小鸟死了而哭半天的女孩子。
她真的会变成赵磊口中那种,冷血无情的女人吗?
我不知道。
我把信收了起来。
接下来的几天,我坐立不安。
那个地址,像个魔咒一样,在我脑子里盘旋。
去,还是不去?
见,还是不见?
我一遍遍地问自己。
最后,我还是决定,去。
就像赵磊说的,我总得给自己一个交代。
我不是去原谅她,也不是去同情她。
我只是想去看看。
看看那个毁了我半生执念的女人,现在,到底是什么样子。
我按照地址,找了过去。
那是一片即将拆迁的老弄堂,到处都是断壁残垣。
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腐烂的味道。
我找到了那个门牌号。
是一栋快要塌了的阁楼。
楼梯又窄又陡,踩上去咯吱作响。
我走到二楼,敲了敲门。
门开了。
开门的是一个女人。
头发花白,满脸皱纹,身形佝偻。
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。
她的眼睛,浑浊,暗淡。
我们俩对视着。
我看着她,她也看着我。
时间,在这一刻,好像静止了。
我认出了她。
尽管她已经老得不成样子,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。
她就是林婉。
而她,显然也认出了我。
她的嘴唇哆嗦着,眼睛里,慢慢地,涌上了泪水。
陈……陈劲?
她的声音,沙哑,干涩,像被砂纸磨过一样。
我点点头。
是我。
她再也忍不住,捂着脸,蹲在地上,痛哭失声。
哭声里,有委屈,有悔恨,有绝望。
我站在门口,没有进去,也没有去扶她。
我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她。
看着这个我爱过,也恨过的女人。
看着她,在我面前,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。
心里,五味杂陈。
没有想象中的愤怒,也没有报复的快感。
只有一种,很深很深的,无力感。
和一种,说不出的悲哀。
我们都老了。
我们都被时间,被命运,折磨得面目全非。
当年的那些爱恨情仇,在残酷的现实面前,好像都成了一个笑话。
她哭了很久,才慢慢地站起来。
她擦了擦眼泪,把我让进屋里。
屋子很小,很暗。
只有一张床,一张桌子,一把椅子。
桌子上,放着一个药瓶。
让你见笑了。她给我倒了一杯水,家里……没什么好招待你的。
我没喝。
你信里说的,都是真的?我开门见山。
她点点头。
我知道你不信。她苦笑了一下,我妈还在世的时候,我问过她。她承认了,信,是她烧的。她说,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跳火坑,再把你拉下水。
她去年走的。走之前,她跟我说,她这辈子,最对不起的人,就是你。
我沉默了。
陈劲,我知道,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
她看着我,眼睛里,带着一丝祈求。
我不是想求你原忘,更不是想让你帮我什么。我车行的事,赵磊也跟我说了,你现在过得很好,我为你高兴。
我只是……只是想把欠了你四十年的那句对不起,亲口告诉你。
她说着,就要给我跪下。
我一把扶住了她。
她的胳膊,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
不用了。我说。
都过去了。
是啊,都过去了。
再多的对不起,也换不回我逝去的青春。
再多的解释,也弥补不了我那五年的等待和绝望。
我们之间,早就清了。
从她坐上那趟火车,从我收到她结婚的消息那一刻起,就两清了。
我没再多说什么。
我从口袋里,掏出一个信封,放在桌上。
里面是我来之前,取的一万块钱。
拿着吧。我说,看病,或者……租个好点的房子。
她愣住了,然后拼命地摇头。
不,我不能要!陈劲,我不是这个意思!
这不是给你的。我看着她,一字一句地说。
这是给当年那个,在东北的小山坡上,给我讲上海故事的,那个叫林婉的女孩子的。
我陈劲,不欠她什么。
但她,也不该是现在这个下场。
说完,我转身就走。
她在我身后,哭着喊我的名字。
我没有回头。
我一步一步地,走下了那个又黑又暗的楼梯。
走出了那条破败的弄堂。
当我重新站在阳光下的时候,我长长地,舒了一口气。
感觉心里,有什么东西,彻底放下了。
我没有原谅她。
我只是,原谅了我自己。
原谅了那个,曾经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,而赌上一切的,年轻的傻子。
人生,就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列车。
我们都会在某个站台,因为一个选择,而走向完全不同的轨道。
没有对错。
只有,承担。
我抬起头,看了看天。
天很蓝,云很白。
像极了1974年,东北那个小山坡上的天空。
只是,我的身边,再也没有那个,指着云朵说像兔子的女孩子了。
云帆服务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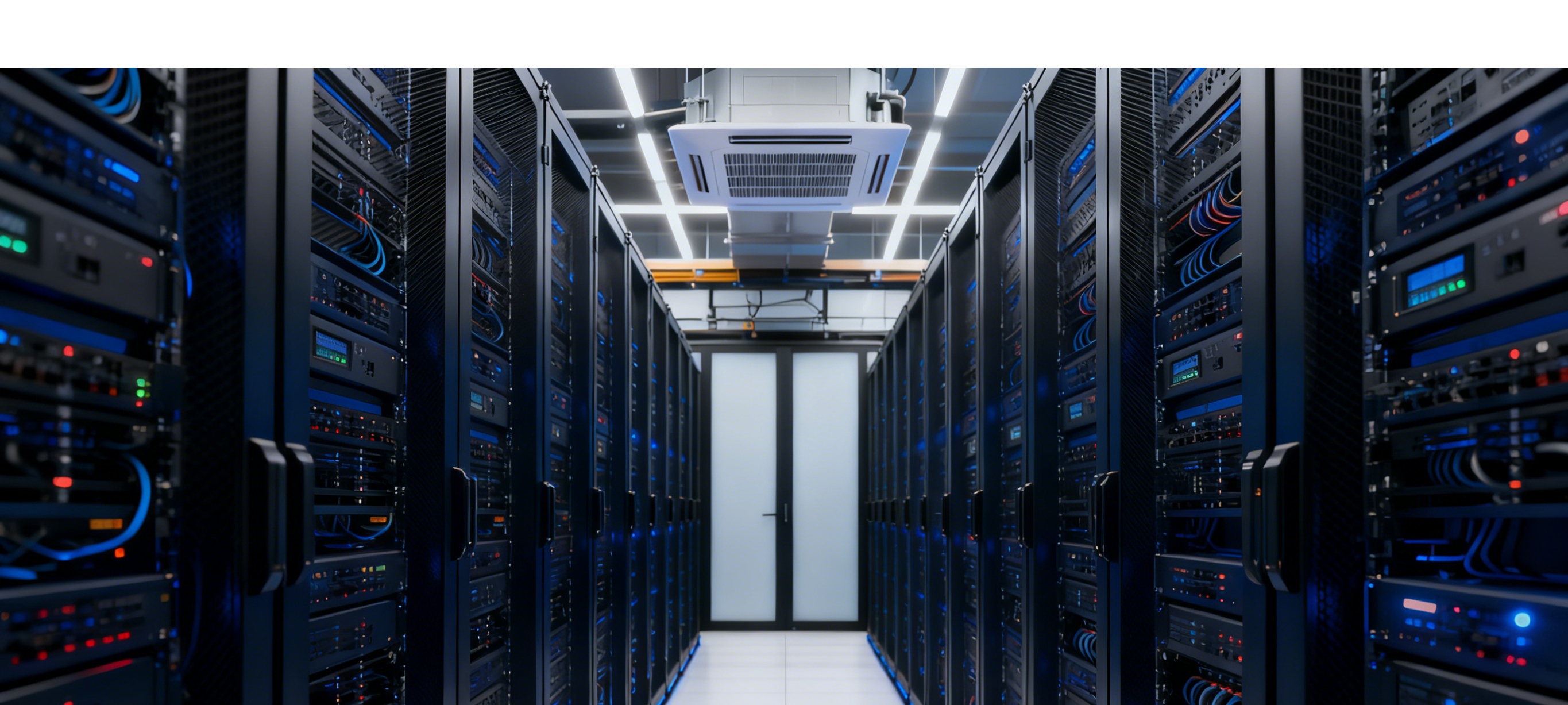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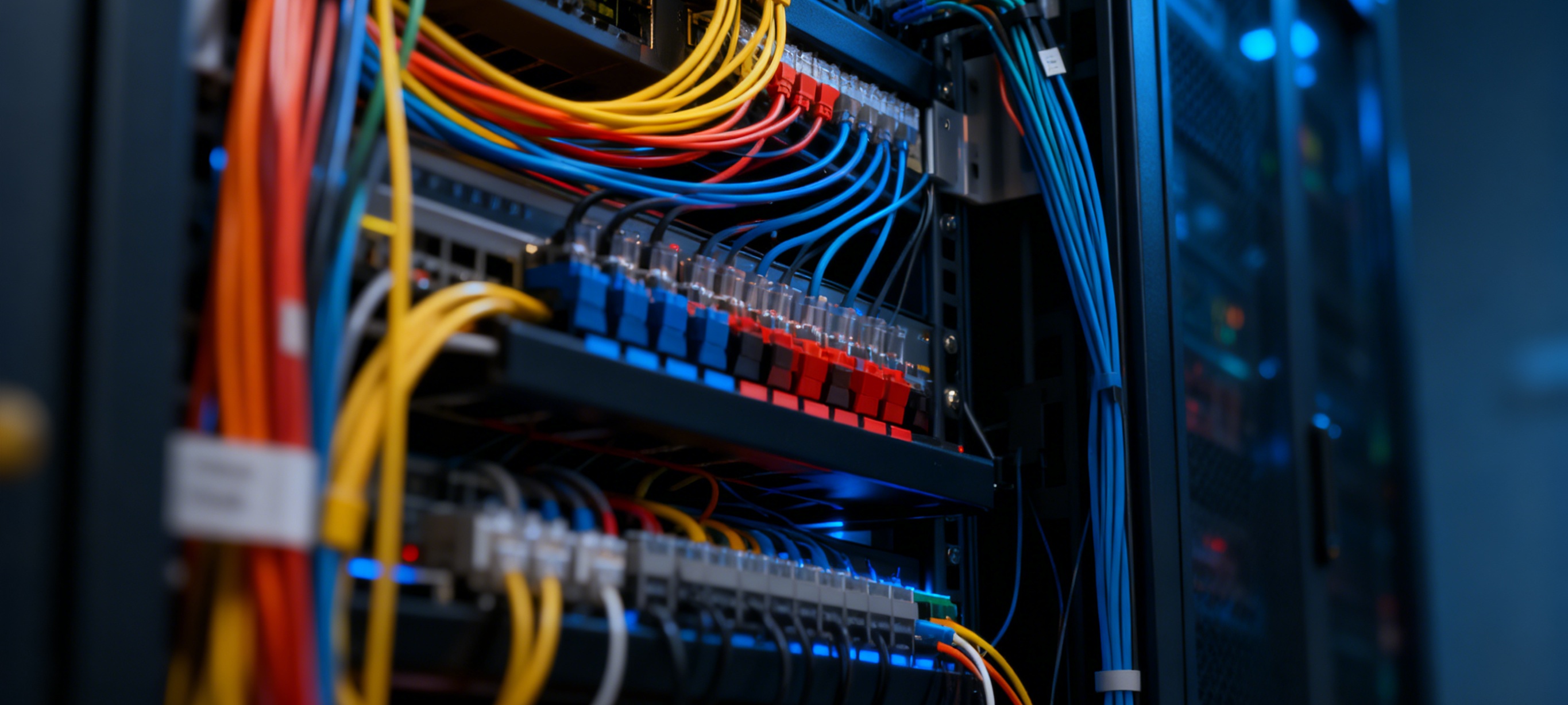
扫码关注
微信好友
关注抖音